讲坛回顾|“疯癫”的生物学、语文学与政治经济学
时间:2023-11-01 点击数量:2022年6月2日,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学研究所“歌乐讲坛”第二十一讲于19:00通过腾讯会议进行。此次讲座由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和文化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张锦老师,主持人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冯亚琳教授。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国内外多所院校的一百多位师生在线与会并参加讨论。

张锦老师首先从写作背景引入,福柯在以整个欧洲史为参照的同时选择了贵族史观来进行知识突围,因为自法国大革命后贵族便被王权和资产阶级放置于历史书写的边缘地带。随后张锦老师介绍了福柯一代人“弑父”行为的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反对右派戴高乐主义以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为范式,转而关注民众的历史议题,重构历史伟人的叙事方式。二是福柯一代逐渐完成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二战后的欧洲思想家希望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发现一种反思欧洲思想史的可能,从而找到历史突围的策略。其方式是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重新审视欧洲近代史,以欲望与文明的阐释方式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宏观叙事。而弗洛伊德等人关注欲望与文明正是因为人口治理处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位置,这也接续了马克思对于劳动和世界市场的分析。人口治理之中还有另一条可解释的线索:性节制。在维多利亚时代,人口处在发展的关键点上,节制性意味着从教育、安全等各方面来节制人口,因此精神分析、欲望阐释学以及性解放构成了反抗的议题。
福柯考察疯癫线索的时间线从16世纪文艺复兴至17、18世纪古典时代再到19世纪精神病院的诞生。张老师总结了福柯考察的三个范式:生物学、语文学和政治经济学。福柯要探究的问题便是在这三个范式产生的19世纪之前,疯癫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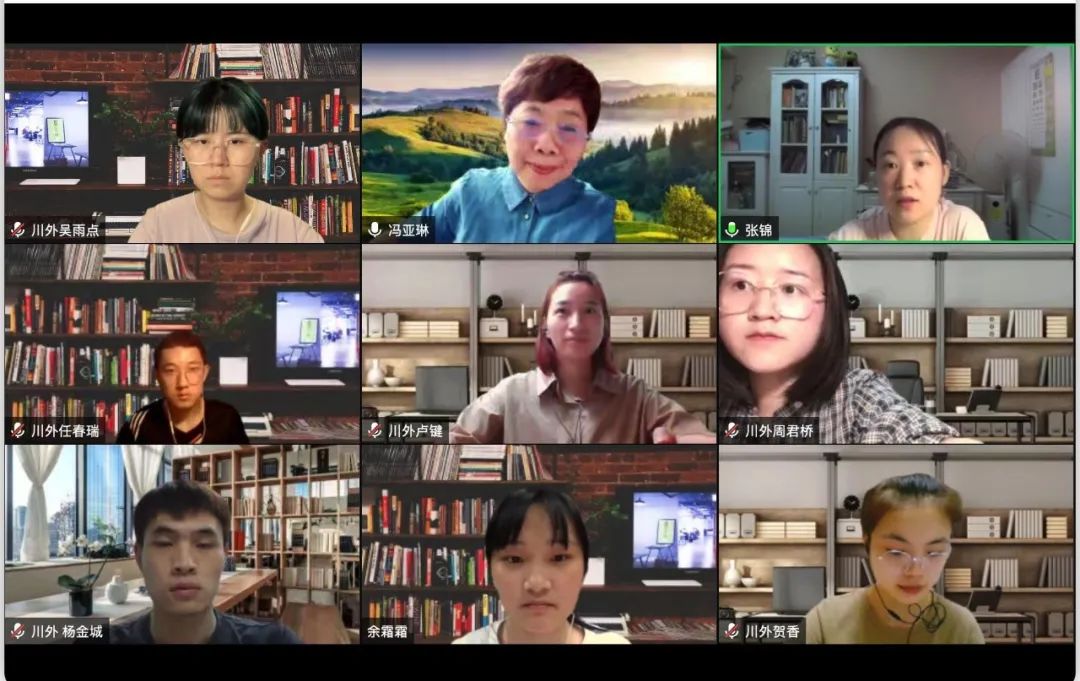
通过历史背景和三个范式演变的铺垫,张锦老师分别介绍了疯癫在三个历史时期所处的位置。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领域中突然出现了“愚人船”这一意象,对疯人和疯癫的书写占据着核心地位。福柯对此做出解释:由于瘟疫和战争,欧洲被死亡这一意象长久笼罩,疯癫被认为是提前的死亡,人们希望通过接近疯癫来认识死亡。疯癫在叙事作品中居于中心,具有结束作品和昭示作品意义的能力。
到了古典时代,禁闭取代了愚人船。1657年巴黎建立了一所用于大规模收容穷人的总医院,被收容者在医院内会进行低成本的劳动。而这样的收容与医学并无联系,实际是一种治安手段,以避免由于经济问题而失业的人群扰乱社会治安。尽管被禁闭起来的疯癫有一定经济意义,但其更重要的是治安意义。古典时代的劳动是一种伦理意识,在劳动体验中,经济与道德交融在禁闭所里。对于17世纪疯癫的含义,张老师借福柯总结道:古典时期的疯癫自愿越出自然阶级秩序的雷池,置身于其神圣的伦理界限之外。禁闭建立了美德与国家大事的关系,决定了古典时期疯癫的体验。除此之外,古典时代疯人被展示和被折磨与耶稣受难相关,具有一种神圣性。古典的理性时代并没有收编疯癫,它仍旧是一个无法抵达的存在,尚且具有一种尊严和意义。
进入19世纪后,欧洲突然出现的监狱热病使人们意识到禁闭是一个错误的经济措施,因为人口是财富的因素,是土地和财产之间的中介。人们对待疯癫的方式由此发生改变。疗养院和精神病院被建立起来,专门收容生理意义上的疯人,疯人成为现代医学的对象。这些机构逐渐演变为监视的地方,医生和护士成为机构的权威,疯人从道德上被矮化为未成年人。家庭也合谋了精神病院的功能。精神病院体现了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和子女的关系,家庭则获得了近代父权制的特有含义。到了19世纪末,疯癫不再具有经济、文化和政治史的重大意义,能够驱走疯癫的只有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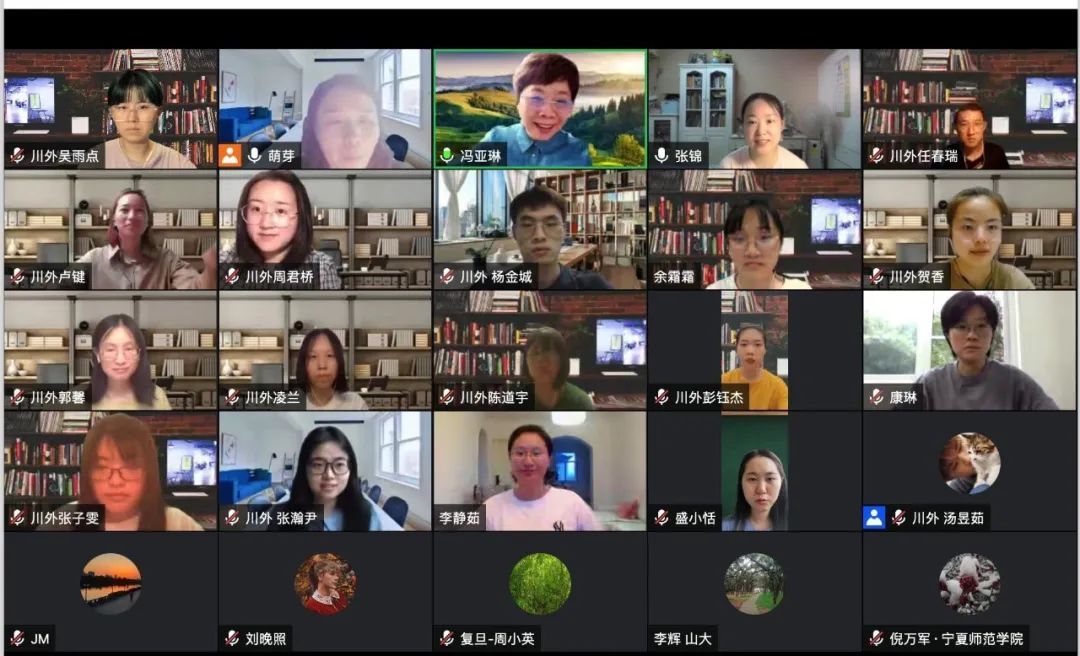
张锦老师最后对所讲内容做了简要总结。16世纪时疯癫存在于社会之中,虽被驱赶于愚人船之上,但疯癫表征了某种意义的智慧;到了17世纪疯癫虽然遭到排斥,但依旧还具有对抗理性的功能;在19、20世纪,疯癫演变成自然现象,即疾病。福柯考察疯癫的过程展示了疯癫主体的形成过程,这既是一个文学实践,也是一个生物学、语文学与政治经济学演变的故事。
在讨论环节,主持人冯亚琳教授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简要梳理后,张锦老师逐一详细解答了与会师生的热情提问,例如福柯的整体论述是否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内、治疗疯癫与旅游文学的关系,自由主义尤其是商业自由和疯癫之间的关系、古典时代民族的概念理解等问题。讲座持续了近三小时,在线师生提问讨论的热情依旧高涨,但仍有诸多问题无法一一讨论。冯亚琳教授和与会师生对张锦老师带来精彩的讲座表示了衷心感谢,并表示期待未来可以进行线下讲座,继续畅谈。文案:张子雯
排版:张子雯
审核:郑萌芽、张瀚尹


